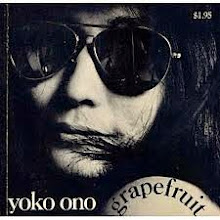噢眼淚。
當年范小姐深情地唱,萬千少男少女跟著同聲和道,噢眼淚‧眼淚都是我的體會‧成長的滋味‧噢眼淚。我也曾那樣聲嘶力竭,卻在唱 「妳說這叫長大,我說多麼的費解」。
轉眼光華,廿五鈴聲響起,那年讀本子裡的驀然回首,還曉得笑談白前輩的廿五樽頸位,現在 雙子女生的樽頸拐到哪兒去了…無法不感慨。閱同道中人的日誌,現實生活,生活於現實,被說服似的低頭幹活,像勤快的工蜂前去後來沒止息地用力遊走,想起黃碧雲書裡所提及的 如若明天我離去,案桌上的工作有沒有第二倈接手,還是大家會發現那些可有可無的二三事,處理與否壓根兒無關痛癢。雖說 我並沒有自我存在的危機,我知道我工作的地方需要我,我知道有些事情的確是自己做得比較好,然而 也曉累。
千萬個夢遊的晚上,迷妳我忙不迭四處走,回到中學時代穿梭於各班房中,等上課等下課趕功課累會考,本本遊書疊在床邊立起精神支柱,給獨我吊命。這半年,多少個不知所謂的夢境再一點一滴抽取精神,當鬧鈴吵醒女生,揉著雙目,人不自覺地嘆口氣。
不要緊。黑雨的那個晚上我像沒睡人,筋疲力盡之下反見回光。很好。我跟大世界圍在一起,然後很快很快,我又進入迴旋,換一件簇新的防衛甲,多少硬仗也不怕。
Tuesday, April 25, 2006
娃兒。
娃兒。
有時候,很想家。不過是數十分鐘車程之隔,卻想得像天涯海角。躺在睡床上,眼角甚至滲出淚水。腦海浮現的是阿母的面容。不要亂想,阿母不是慈祥可譪的那一種,她精明聰慧正氣但霸道,我自覺有點像她,卻不夠世故聰明。
終日披著防衛甲到處戰鬥,落得沙鹿四周滿臉傷痕,停下來尚不敢哭,生怕敵人就在咫尺之近。累了,跑到阿母床邊,在冷風吹送之時,閉上眼好好安睡,用性命擔保,她不會在妳脆弱時攻擊閣下。嗯。無夢才算休息。
讓五月夏成新天,閉目幻想像family stone裡面的女兒,挻著大肚,慢慢挪移到母親背後,雙手環保,沉沉休息睡去。誰知何時末日,我總感激沿途有妳。
有時候,很想家。不過是數十分鐘車程之隔,卻想得像天涯海角。躺在睡床上,眼角甚至滲出淚水。腦海浮現的是阿母的面容。不要亂想,阿母不是慈祥可譪的那一種,她精明聰慧正氣但霸道,我自覺有點像她,卻不夠世故聰明。
終日披著防衛甲到處戰鬥,落得沙鹿四周滿臉傷痕,停下來尚不敢哭,生怕敵人就在咫尺之近。累了,跑到阿母床邊,在冷風吹送之時,閉上眼好好安睡,用性命擔保,她不會在妳脆弱時攻擊閣下。嗯。無夢才算休息。
讓五月夏成新天,閉目幻想像family stone裡面的女兒,挻著大肚,慢慢挪移到母親背後,雙手環保,沉沉休息睡去。誰知何時末日,我總感激沿途有妳。
Wednesday, April 19, 2006
昏迷。
昏迷。
就不能禮貌一點談昏迷,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像對不起父母跟身邊人,像對不起那些想甦醒的,像對不起部份野心勃勃的自己。
有那麼一刻,我想昏迷,如像躲在睡夢中不想醒來。睡一覺的,不想白白每天受壓,抽不起身的累意走進微血管,慢慢流動,直達身體上下左右每個角落,無可倖免。於是在迷糊的似醒還在睡的狀態下,我又再一次穿起校服,趕往科場,時鐘指示,晚了晚了,無法拯救的晚了。
無可否認,最近是比較苦。用「捱」日子來形容又未免太可憐,可是我還是有一份「在捱」的心情。怎麼可能把這情況說得清楚一點…..於是我唯有咬著指頭邊用力思索。
我經常告訴自己,如若生活有不能承受的壓力,吸口氣,推卻所有,然後大步走。
就不能禮貌一點談昏迷,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像對不起父母跟身邊人,像對不起那些想甦醒的,像對不起部份野心勃勃的自己。
有那麼一刻,我想昏迷,如像躲在睡夢中不想醒來。睡一覺的,不想白白每天受壓,抽不起身的累意走進微血管,慢慢流動,直達身體上下左右每個角落,無可倖免。於是在迷糊的似醒還在睡的狀態下,我又再一次穿起校服,趕往科場,時鐘指示,晚了晚了,無法拯救的晚了。
無可否認,最近是比較苦。用「捱」日子來形容又未免太可憐,可是我還是有一份「在捱」的心情。怎麼可能把這情況說得清楚一點…..於是我唯有咬著指頭邊用力思索。
我經常告訴自己,如若生活有不能承受的壓力,吸口氣,推卻所有,然後大步走。
Monday, April 17, 2006
心血太少
心血太少
漏斗假裝心臟,為容器注滿點滴,定時定候把器皿倒轉,目的就是要點滴一直流動。
想太多。沒空用塔羅為自己算算到底該想多少。那天晚上,跟qw的友好留於白素房子內,小黑犬的四蹄像時針訴說著流逝,談起什麼是想太多。想太多。誰有能耐知道什麼是太多,在哪個位置停下來最好。人兒無法什麼都不想,尤其是像我們這種本來就因為有頭腦所以感到自豪的人,更難。
早上醒來,晨光明媚得帶點揶揄的味道,我知道,知道今天是公眾假期,大家都在放輕鬆。滲著冷風的陽光,揉合四周的風景,我們的城市 就這樣在日光中黑夜裡停不了地更新。無法言喻的程序在運作,像誰也沒能耐跑出那缺口。
漏斗假裝心臟,為容器注滿點滴,定時定候把器皿倒轉,目的就是要點滴一直流動。
想太多。沒空用塔羅為自己算算到底該想多少。那天晚上,跟qw的友好留於白素房子內,小黑犬的四蹄像時針訴說著流逝,談起什麼是想太多。想太多。誰有能耐知道什麼是太多,在哪個位置停下來最好。人兒無法什麼都不想,尤其是像我們這種本來就因為有頭腦所以感到自豪的人,更難。
早上醒來,晨光明媚得帶點揶揄的味道,我知道,知道今天是公眾假期,大家都在放輕鬆。滲著冷風的陽光,揉合四周的風景,我們的城市 就這樣在日光中黑夜裡停不了地更新。無法言喻的程序在運作,像誰也沒能耐跑出那缺口。
Wednesday, April 12, 2006
心癮
我跟自己說,不要寫。
不是在訴說生活不如意,著實我過得很好,不過是有點累。
不要寫,是因為想好好全身全心休息。寫作像讓腦袋做運動,雖喜歡卻也疲累。
但心癮起的時候,一下子又按捺不住,雙手自由在鍵盤上遊走。
瑪莉想游泳,可是現在還是嚴冬。我提議她到暖水池玩玩,她搖搖頭,不要。用王琦瑤的語氣說,不要。唉。女生像王琦瑤,不好。命不好。於是我著她不要用這種聲線說話,她掃掃裙擺,怎麼了,是什麼回事? 於是我不想再提了。
小生最近喜歡哭,看電視的時候哭 跟舊人通電話會哭 甚至獨個兒臨睡前也會哭。就這樣,他來找我,說想談談天,生怕自己快要得抑鬱症。於是 我小心翼翼跟他對答,怕稍一不慎讓別人難憾。他說阿父不喜歡他像個女生。就在那刻,我覺得他壓根兒是個女生。
芠芠肚很漲,口很乾,卻又不敢飲水,因為回到最初,肚很漲。我用手按按她的小肚子,這胖女生,怎麼食得那麼多。她說,心裡很難過,每次咬一口就狠不得摑自己一把掌。
不是在訴說生活不如意,著實我過得很好,不過是有點累。
不要寫,是因為想好好全身全心休息。寫作像讓腦袋做運動,雖喜歡卻也疲累。
但心癮起的時候,一下子又按捺不住,雙手自由在鍵盤上遊走。
瑪莉想游泳,可是現在還是嚴冬。我提議她到暖水池玩玩,她搖搖頭,不要。用王琦瑤的語氣說,不要。唉。女生像王琦瑤,不好。命不好。於是我著她不要用這種聲線說話,她掃掃裙擺,怎麼了,是什麼回事? 於是我不想再提了。
小生最近喜歡哭,看電視的時候哭 跟舊人通電話會哭 甚至獨個兒臨睡前也會哭。就這樣,他來找我,說想談談天,生怕自己快要得抑鬱症。於是 我小心翼翼跟他對答,怕稍一不慎讓別人難憾。他說阿父不喜歡他像個女生。就在那刻,我覺得他壓根兒是個女生。
芠芠肚很漲,口很乾,卻又不敢飲水,因為回到最初,肚很漲。我用手按按她的小肚子,這胖女生,怎麼食得那麼多。她說,心裡很難過,每次咬一口就狠不得摑自己一把掌。
Thursday, April 06, 2006
開關。
體內應當安裝數以百萬的開關制,如同gene內的dna,成千上萬過億,把每種行為動作心情外表分得清清楚楚,不要重覆不要混雜。
「啪」,就這樣,彷如關燈,從此以後不再有天亮。
工作勞累,背負的無形可如煙輕也可如千斤。忘了從哪裡聽說過,翅膀只長在有夢的人身上。成飛鳥,如海鷗般高速飛馳。
「啪」,我要休息了。
「啪」,就這樣,彷如關燈,從此以後不再有天亮。
工作勞累,背負的無形可如煙輕也可如千斤。忘了從哪裡聽說過,翅膀只長在有夢的人身上。成飛鳥,如海鷗般高速飛馳。
「啪」,我要休息了。
Tuesday, April 04, 2006
線話。
線話。
幼長幼長,繾綣之際,在瞬間我們開始對話。
有沒有好好睡睡? 有沒有因為談情所以跳舞?
偶然我學著一根冰條的硬生生站立、偶然我學著一根草般無方向感。或且因為多變,開始有人跟我說話,有人喜歡跟我說話。也好。說啊說,說啊說,像對著電腦螢光幕不停胡亂打字。沒重心,像言辭再沒意思地胡亂廢噏。
左右手一同用力,拉開咖啡粉的包裝,滾水衝啊衝,香氣四溢,我只能說 大家都是勤快工作的人兒。可惜 工蜂螻蟻,我們誰願意甘心命抵。向著目標跑,永遠追著甫出生便擺放在前端的金線球,像驢兒追著的那口紅蘿蔔,竭盡所能便為那一口,爽快的一口。
這種話,甫一開始,又怎能完滿結束。
幼長幼長,繾綣之際,在瞬間我們開始對話。
有沒有好好睡睡? 有沒有因為談情所以跳舞?
偶然我學著一根冰條的硬生生站立、偶然我學著一根草般無方向感。或且因為多變,開始有人跟我說話,有人喜歡跟我說話。也好。說啊說,說啊說,像對著電腦螢光幕不停胡亂打字。沒重心,像言辭再沒意思地胡亂廢噏。
左右手一同用力,拉開咖啡粉的包裝,滾水衝啊衝,香氣四溢,我只能說 大家都是勤快工作的人兒。可惜 工蜂螻蟻,我們誰願意甘心命抵。向著目標跑,永遠追著甫出生便擺放在前端的金線球,像驢兒追著的那口紅蘿蔔,竭盡所能便為那一口,爽快的一口。
這種話,甫一開始,又怎能完滿結束。
Monday, April 03, 2006
l.i.n.g.
這不是最漂亮的窗,但娃兒在月亮低下想念舊人。
由陌生人開始,到相交至深,如傾城之戀中所提及的執子之手。執子之手,成「摯」一字,貼心曾道,能執子之手,即使無法到老,也不枉相識一場。能聰明點,或能早早得悉那天意/人願。
進入社會以後,輪轉,找尋並同時失落,想美化的話我們可以說成在童話故事結束之後,進入了圖書館成人部,有血腥有暴力有憐憫有深不可測有在徊走在現實及夢想之間的愛情也有離開及離不開的理想跟前途。
張愛玲當年所寫的傾城之戀,因為遭受壓迫的家因為翩翩起舞的風度及柔情因為動盪的時代因為尚有點血肉的心情,造就成偉大的愛情故事。跟半生緣比,還是有段距離。傾城是因為天地都塌陷,人兒無法想像往後,就讓我們守在一起的激情就此存檔。然而半生緣 不同,我喜歡她那輕妙如煙的道理。糾纏數年,苦戀半生,來來回回我們就是無法返回起點,也不能到達終點。用周星馳語氣說前句: 「人世間的所有悲歡離合」,「往往是人為的」(後句是我說的)。像半生緣,在此世代,自由度如此大,不會再有曼露的出現,曼幀太可安心等待,跟朗君如形隨影亦可。
註: 電影節來臨。請盡量忘憂。
由陌生人開始,到相交至深,如傾城之戀中所提及的執子之手。執子之手,成「摯」一字,貼心曾道,能執子之手,即使無法到老,也不枉相識一場。能聰明點,或能早早得悉那天意/人願。
進入社會以後,輪轉,找尋並同時失落,想美化的話我們可以說成在童話故事結束之後,進入了圖書館成人部,有血腥有暴力有憐憫有深不可測有在徊走在現實及夢想之間的愛情也有離開及離不開的理想跟前途。
張愛玲當年所寫的傾城之戀,因為遭受壓迫的家因為翩翩起舞的風度及柔情因為動盪的時代因為尚有點血肉的心情,造就成偉大的愛情故事。跟半生緣比,還是有段距離。傾城是因為天地都塌陷,人兒無法想像往後,就讓我們守在一起的激情就此存檔。然而半生緣 不同,我喜歡她那輕妙如煙的道理。糾纏數年,苦戀半生,來來回回我們就是無法返回起點,也不能到達終點。用周星馳語氣說前句: 「人世間的所有悲歡離合」,「往往是人為的」(後句是我說的)。像半生緣,在此世代,自由度如此大,不會再有曼露的出現,曼幀太可安心等待,跟朗君如形隨影亦可。
註: 電影節來臨。請盡量忘憂。
急
「人有三急」,找洗手間的夢境我估計大家都試過。一直以為是我睡飲水的習慣使然,近日友人相告,才知曉原來夢中的「放水」是釋放情緒的示意。
我經常夢到「緊急來潮」,想要「放水」,卻找來找去也找不著可用的洗手間。有時是洗手間太髒,有時是洗手間沒有門,有時是人多太,直至找到最decent的,卻發現有許多只花貓在看。
友人說,這代表「生活尚未有夠私人空間」:privacy。喎。
自在空間,歷年來首次遇到這方面的難題。
我經常夢到「緊急來潮」,想要「放水」,卻找來找去也找不著可用的洗手間。有時是洗手間太髒,有時是洗手間沒有門,有時是人多太,直至找到最decent的,卻發現有許多只花貓在看。
友人說,這代表「生活尚未有夠私人空間」:privacy。喎。
自在空間,歷年來首次遇到這方面的難題。
Subscribe to:
Posts (Atom)